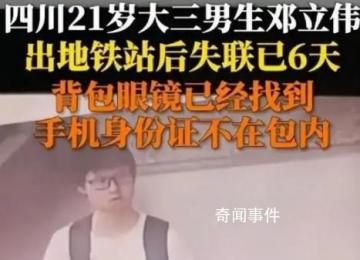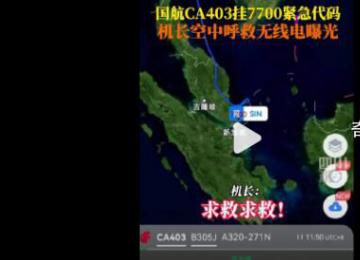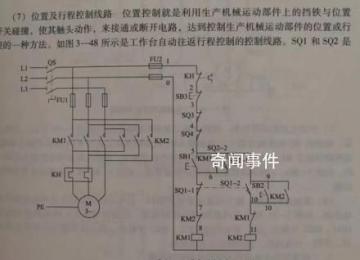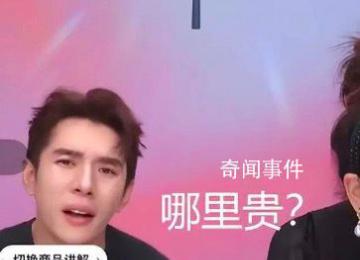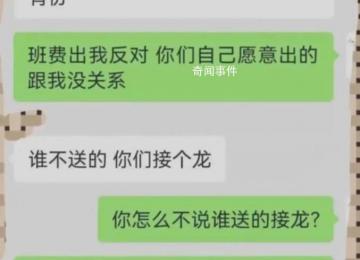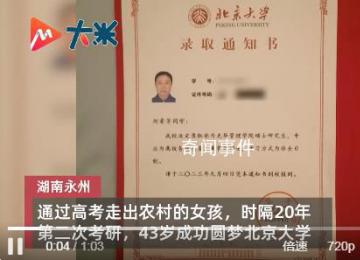生死急診室:2分鐘接診一個病人
導讀:一周7天,10080分鐘,急診科醫生孫東輝陀螺一樣轉個不停。2023年第一周,他所在的三甲醫院急診和發熱門診每天涌入1000多人,是平時的一倍多

一周7天,10080分鐘,急診科醫生孫東輝陀螺一樣轉個不停。
2023年第一周,他所在的三甲醫院急診和發熱門診每天涌入1000多人,是平時的一倍多。醫生們相當于不到2分鐘就要接診一個病人。孫東輝耳邊除了醫療器械的“嘀嘀”聲外,聽到最多的就是,“醫生,快來。”
剛給一位老人插上管,孫東輝耳邊再次傳來急救聲。他是某三甲醫院醫生。
“快!患者高燒、暈厥,呼吸心跳驟停!”同事在一旁大喊。孫東輝沖過去,對患者實施胸外心臟按壓。氣管插管、使用呼吸球囊,將搶救藥物通過靜脈注入體內也幾乎在同一時間,一氣呵成。
幾分鐘后,患者從死亡線上回來了。孫東輝舒了口氣。
這是發生在1月1日晚上8點多的一幕。這些在外人看來驚心動魄的搶救場景,對孫東輝而言早就是家常便飯。這一個多月來,他所在的急診大廳每天熙熙攘攘,猶如春運。
孫東輝就職的這家三甲醫院,在華北地區名氣頗高,是當地收治患者最多的醫院。疫情政策放開后,醫護人員面臨的壓力更是前所未有。“最近急診和發熱門診每天都來1000多人,是平時的一倍多。”孫東輝說,相當于24小時不停歇,不到2分鐘就要接診一個病人。其中近一半患者超過65歲,幾乎需要搶救。
為了保證這段時間人手充足,醫院將600多名醫護人員“釘”在了急診和發熱門診上,24小時輪班工作,大多人吃住在醫院。新的一年開始了,但對他們來說并沒有什么改變。
2023年第一周,仍有數不清的病人從四面八方涌入急診大廳。
由于沒有足夠的床位,患者們多會自帶折疊床,在急診大廳找空隙躺下,等待醫生問診。陪同家屬一臉茫然地穿梭在密密麻麻的輸液架和氧氣罐之間。
急診大廳溫度很高。隔著N95和面罩,孫東輝能感受到黏稠的空氣吸入鼻腔:“既有病患呼出的氣體,也有消毒水和藥物的味道,太難受了。”
“醫生,快來”
快一個月了,孫東輝一直沒回家。雖然每天只上8小時小夜班(17點-24點),可他擔心將病毒帶回家,索性吃住在醫院,家里大小事情都顧不上。
這意味著,只要一穿上防護服,就要在8個小時內不吃不喝,也盡量不上廁所。
孫東輝所在的急診科,是全年、全天不間斷接診的部門。新冠疫情以來,他們既要落實防疫要求,又得保證急診質量。防控政策放開后,大家本以為能輕松些,可隨之而來的是大量陽性患者和有基礎病的人。
正式進入急診大廳前,患者要先在門口預約分診登記、量體溫、測抗原,每一步都有醫護人員陪同。這部分工作多由實習生承擔。完成這些前置程序后,醫生會根據情況,將患者分為5個等級——危急、危重、急癥、輕癥、非急。前三種病癥,救治時間最短不能超過半小時,后兩項則至少要等一兩個小時,甚至4個小時。
確定等級后,危急病人會被送入單獨病房,危重患者則能分到有很多床位的紅區病房,急癥人員被安置在急診大廳一側的黃區病床上,其他人要在大廳里的綠區耐心等待。
也因此,紅區、黃區、綠區的醫護人員會呈現出兩種工作狀態——前兩個區域一直在插管、上呼吸機、心肺復蘇,后者多是查體、抽血、輸液。
孫東輝最擔心的還是那些危急患者,尤其是感染了奧密克戎的危急患者。
1月2日晚上10點多,救護車送來一位發燒且無法自主呼吸的老人。孫東輝和同事接診后,馬上對其進行緊急氣管插管搶救,老人癥狀稍稍得以緩解。隨即,這位老人又檢測出新冠陽性,雙肺已嚴重感染。由于該類老人普遍有基礎病,抵抗力非常差,會給治療帶來諸多復雜性,孫東輝趕緊聯系其他科室進行會診。
剛處理完老人的事,急診又來了一位陽性的主動脈夾層病人。這位60多歲的男性不僅胸部疼痛,血壓也急劇下降。并且,他的胸主動脈隨時有破裂可能,必須馬上手術。于是,孫東輝又趕緊聯系相關醫生。
處理完這名患者的情況,已經24點了。孫東輝拖著疲憊的身軀和大夜班(24點—早上8點)同事交接,按程序脫掉防護服,給自己全身消毒,開始吃飯、洗漱。
真正入睡是凌晨兩點以后了。躺在宿舍的床上,他終于有時間好好看手機——幾乎每次下班,他都能收到幾百條微信,大多是親戚朋友發的,內容無非是咨詢病情或想讓其安排住院。對于詢問病情的人,孫東輝能答盡答,但對想找關系的朋友,他婉拒了。每天處理完這些事情,他才能安心入睡。
按照醫院的制度,孫東輝可以休息一整天。但他白天睡不著,近段時間因為人手不足,他常被急診拉過去幫忙。
下午5點,孫東輝又開始了小夜班。1月3日這晚,他剛接班,救護車就將一名陽性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送到急診。孫東輝馬上為他插管,恢復心跳等生命體征后,又趕緊聯系手術事宜。這個病患才放下,又一名抗原陽性老人過來了。老人說自己突然四肢無力、頭暈惡心,脖子疼痛難忍。孫東輝和同事趕忙安排其查CT、做核磁,發現是多種腦部疾病,馬上又安排手術。
事實上,這些危急病人,孫東輝后期根本不用再管,但有時他會多問幾句。比如前幾天,一個中年女性患者“轉陰”后突發心肌炎,轉入重癥醫學科。
這段時間來了很多“轉陰”的心肌炎病人,孫東輝也想知道到底該怎么治療。他主動問了重癥醫學科醫生,對方說:“給她聯合了IABP(主動脈球囊反搏)和ECMO(人工肺)治療,恢復情況很好。”
了解完情況,孫東輝轉過頭繼續忙手頭的患者,給他們上呼吸機、支氣管鏡、氣管插管、吸痰……站在紅區和黃區的病床前,他耳邊除了醫療器械的“嘀嘀”聲外,聽到最多的便是:“醫生,快來。”
可有時候醫生確實沒法及時趕到——一是忙不過來,二是被防護服包裹的他們,聽力會受到些許影響。孫東輝和同事也總因為沒能及時回應患者疑惑,而被家屬謾罵指責。
他委屈,但也沒辦法,“每個人都有手機,我要敢還嘴,人家一拍發網上,不僅毀了自己,醫院名聲也會受損。”他忍得了謾罵,但有一類事情總讓他揪心——由于平時極少有時間關心家人,很多醫護人員往往直到家人來急診看病時,才知道他們病了。一提到這些,孫東輝就有些控制不住情緒,“作為醫生,連家人都無法保護,我們肯定是失職的。”
1月4日晚,他一個同事的父親到急診看病,這位同事和父親說了不到一分鐘話,門外又來了輛救護車。
車上下來的是一名70多歲的老人,新冠陽性,發燒數日,胸悶氣短。經過檢查,老人不僅肺部有問題,血氧飽和度也在下降。孫東輝和那位同事趕緊給他氣管插管,上呼吸機。
忙完手里的活,這位同事找不到自己的父親了。她打了電話才知道,父親已經去了另一家醫院,“你們這太忙了,我也沒那么嚴重,你快忙吧。”
掛了電話,這位同事在原地哭了起來。
綠區與折疊床
相比對重癥患者的救治,急診大廳的綠區顯得有些“草率”——這個區域的患者病情相對較輕,更多時間里,他們在等待與忍受。
沒有危急、危重病人需要搶救時,孫東輝經常在綠區待著。由于病患太多,整個區域顯得慌亂嘈雜。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過去,都是黑壓壓一片。護士推著轉運床、配送物資小車,不停在人群中穿梭。
綠區沒有病床,只有些用于輸液的椅子。椅子上永遠坐著人,新來的病患只能自己找地方躺下或坐著。醫生和護士甚至會提醒一些家屬,去醫院附近買張折疊床。
也因此,不斷有人拎著折疊床進來。這種簡易床每個售價100元,有人用完后,會低價出售給其他患者。至于床放到哪里,醫院根本不管,哪里有位置,就塞在哪里。
隨著大量病患涌入,急診大廳、診室走廊、藥房前側、廁所旁邊以及任何一個犄角旮旯,都擺滿了折疊床,床下放著夜壺、洗臉盆、洗漱包和各種顏色的被褥。床上躺著的多是老人,他們大多眼睛緊閉,在呻吟聲中消磨生命,家屬或在旁鼓勵,或呆呆地坐在馬扎上一言不發。
“大多都有基礎病,這段時間過來的,又多是肺部感染。”孫東輝直言,輕癥病人雖然比較好處理,但除了輸液外,很多人也得吸氧、做心電監測。
在綠區的醫護人員絲毫沒有自己的時間——他們只要一出現,馬上會被圍得水泄不通,有人問診,有人讓看片子,有人需要換藥,每個人都火急火燎。
事實上,雖然劃分著綠、黃、紅幾個區域,但在實際工作中早就混亂了。“這里流動性太強,患者病情變化又快,每個人必須有更迅速的處置能力。”孫東輝透露,綠區也有不少危重病人,因為醫院騰不出床位,只好讓他們躺在這里。
這意味著,綠區的醫護人員每天也要面對生命垂危的患者——意識障礙、呼吸衰竭、腦血管病、室顫……這些人不是上呼吸機,就是插著管。
1月5日上午,孫東輝起床后到急診室幫忙。他剛換上防護服,一名老年女性患者被救護車送過來,轉運車旁邊是患者的兒子:“醫生!我媽意識模糊了,能先救她嗎?”
沒有遲疑,孫東輝和同事趕緊將面色發紫、脈搏正消失的患者放到綠區。接著進行胸外按壓、插管、吸氧等一套流程,總算將患者暫時救了回來。
1月6日晚上,再次有特殊病人被送到綠區。這名男性老年患者發著高燒,呼吸困難,血氧度60%。由于家屬不知道老人是否感染新冠,醫護人員只好一邊搶救,一邊做核酸。
插管后,老人轉危為安,核酸結果顯示為陽性。孫東輝和同事稍稍緊張了一下,趕緊叫來工作人員對所涉區域進行消殺。
“我們倒不是怕被感染,主要是感染后減員太嚴重了。”孫東輝說,前段時間,他超過三分之二的同事都陽了,最近大家陸續轉陰后,情況才好一點。在他看來,醫護人員只要感染,來急診的患者就可能喪命。孫東輝至今未感染,但他每天仍然緊張,他不想在特殊時期倒下來。
1月6日晚上10點多,孫東輝一個同事突然低燒。沒等她緩一下,救護車拉來一名70多歲的大爺。大爺意識不清、呼吸困難,血氧度只有50%。
“搶救!”孫東輝大喊了一聲。那位同事馬上打起精神,為患者插管、上呼吸機、心電監護……當患者有所好轉時,他們開始詢問其病史、檢查、安排CT。一整套動作完成后,孫東輝發現那位同事一直在掉眼淚。
孫東輝讓她趕緊休息。“稍等會兒吧,還有好幾個喊著換藥呢!”同事說完,推著配送物資的小車繼續穿梭在綠區人群之中。
剛換了沒幾瓶藥,一名懷孕8個月的孕婦被救護車拉到急診。孕婦在家燒到39.2度,抗原顯示為陽性。沒有選擇,正發燒的護士馬上加入救治隊伍。
孕婦被分流到相關科室后,救護車又送來一名發著高燒的7歲女童。女孩因伴有遺傳病,生命體征不穩定。孫東輝的同事馬上進行救治,并迅速聯系兒科大夫。所有這些忙完,又是夜里12點了。發燒的護士脫掉防護服,走進急診大廳,讓同事為自己掛上了輸液瓶。
大夜班的同事接班后,急診大廳繼續忙碌著。
“醫生,快一點”“血壓沒了,心跳沒了”“趕緊插管”“又來一個”……
為患者搏命
在孫東輝的觀察中,2023年第一周,來急診的人少了些,但總體還是高出之前許多,“目前在急診逗留的,多是其他病癥的陰性患者,陽性人員直接引到發熱門診了。”
而發熱門診和急診一樣忙碌——因為人手不足,醫院臨時抽調了很多科室的人去支援,連口腔科醫生都沒放過。
發熱門診在急診大廳外的角落里,經過此處的人們難免下意識加快腳步。
早期的發熱門診只有30張床,后來增加到50張。這段時間陽性重癥患者激增后,醫院又在其他病房樓騰出近300張床位,用于急診、發熱門診分流過來的陽性病人。
發熱門診也是24小時開診,接待的陽性患者既有發燒、頭暈、胸悶的常見癥狀,還有很多腫瘤、心梗、腦梗患者,以及孕婦和兒童。每天都有上百人需要呼吸機,還有少量人員得用ECOM(人工肺)。
除了發熱門診,孫東輝所在醫院的重癥醫學科也承受著巨大壓力——這個被稱為“生命最后一道防線”的部門,就是公眾常說的ICU。
該科室一位護士透露,“送到這里的病人大多無法自理,我們得24小時照料,稍有不慎就可能讓患者喪命。”近段時間很多醫護人員因此放棄了休息,每天連續工作20個小時早就是常態了。“我最怕聽急診打來的電話。”這位護士說,她只要聽到“呼吸衰竭”“多器官衰竭”“心跳呼吸驟停”等詞語,心里就會一激靈。
這場“戰役”中的醫護人員,沒有誰是輕松的。
孫東輝透露,除了大家熟知的呼吸科外,神經內科、骨科、血液透析科、麻醉科、血庫等也早都被調動起來了。比如,腦血管疾病屬于神經內科,冬季本就是這類病癥的高發期,加上疫情因素,這個科室變得格外忙碌。最近,一位有腦血管疾病的老人突發疾病,他不僅是陽性感染者,血氧度也在急劇下降。最終,急診聯系神經內科后,老人被搶救過來。
再比如骨科。由于陽性重癥太多,該科室很多病房直接改成隔離病區。科室人員每天做的多是轉運病人、交接病歷、整理床位等體力工作。
還有后勤保障人員。孫東輝透露,這段時間,食堂的工作人員每人每天都要工作12小時以上,凌晨4點起床,早上6點多必須將數百人的飯菜做好。消殺及保潔人員則需要24小時待命,“一桶消毒液幾十公斤,消殺人員幾乎全天在背著。”孫東輝想想都痛苦。
隨著大家普遍陽過一輪后,醫院各部門的人員壓力稍小了些,但他們或將面臨新的壓力。
自 1月8日開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從“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實施“乙類乙管”后,官方對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實行隔離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觸者;不再劃定高低風險區;不再對入境人員和貨物等采取檢疫傳染病管理措施,對新冠病毒感染者也會實施分級分類收治,并適時調整醫療保障政策。
這當然是基于醫學專業判斷的改變。但也有病毒學專家擔心,在國內疫情尚未過峰的情況下,藥品、醫務人員都較為緊缺,“乙類乙管”可能將對醫療資源造成巨大壓力。
在孫東輝看來,壓力是肯定存在的,他們能做的,就是繼續精細化就診流程。“其實,作為急診醫生,我幾乎感受不到什么(變化),每天依然忙忙碌碌。”孫東輝甚至可以預見,春節前后,自己不會有私人時間。
1月7日下午5點,他剛接班,已經有6個病人在等他處置了。正要開工,門外又來了一輛外地救護車。車上下來一名40多歲的女子,孫東輝詢問她的病情,她只是一直說,“喘不上氣,喘不上氣”。
孫東輝掃了一眼黃區和綠區,竟找不到一個能讓她躺下的地方。他和急救人員抬著患病女子到處找地方,最終在離廁所幾米處,看到一塊2平米左右的空地,就地進行診治。
大廳外,兩輛救護車呼嘯而來,閃爍的車燈在冬日的黑夜里格外刺眼。
“一周7天,10080分鐘,我們時刻都在為患者搏命。”孫東輝現在最大的期許,就是希望春天趕緊到來。
-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禁止網民評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對網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很快便引起了社會大眾對于5個月前,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將及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禁止網民評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對網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很快便引起了社會大眾對于5個月前,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將及 -
 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的隊伍。這支
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順拐同學們組成了方隊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的隊伍。這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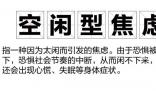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卷加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卷加 -
 網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檢查2023-09-16 16:38:53據國家稅務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網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網絡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網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檢查2023-09-16 16:38:53據國家稅務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局網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網絡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
 恒大人壽嚴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圳監管局官網公布《關于海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保
恒大人壽嚴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險處置再進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圳監管局官網公布《關于海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保 -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王耀慶卻因為悲傷而哭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王耀慶卻因為悲傷而哭 -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站列入專項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塔斯社15日報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站將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稱,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站列入專項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塔斯社15日報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站將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稱,這是基輔政權的又一次 -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荔枝新聞報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行敲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荔枝新聞報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行敲 -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袁冰妍存在涉稅風險,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聯企業存在偷逃稅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部門通過分析發現袁冰妍存在涉稅風險,經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聯企業存在偷逃稅 -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