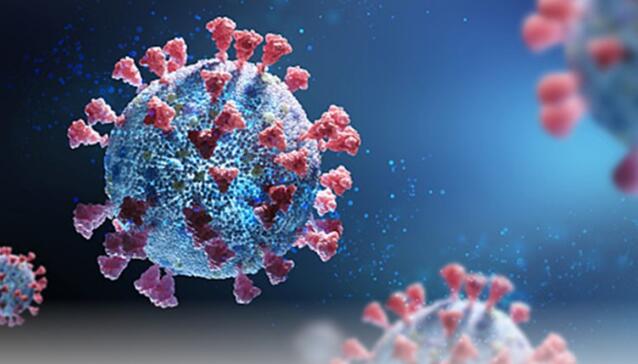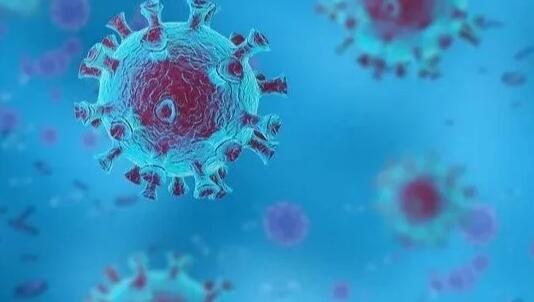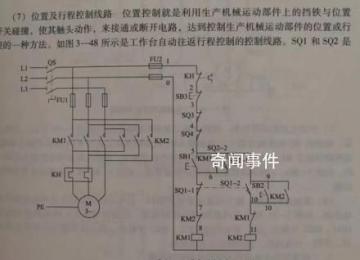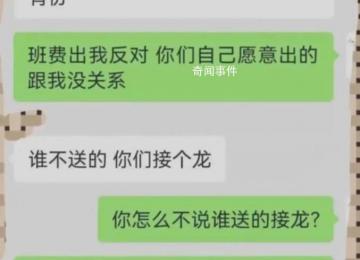新冠抵達(dá)縣城一個(gè)月:90歲老人渡劫
導(dǎo)讀:在不到半個(gè)月的時(shí)間里,奧密克戎就已經(jīng)侵?jǐn)_了全國大部分的縣城、鄉(xiāng)鎮(zhèn)乃至村莊。王玉蘭所屬的縣處于中部省份,常住人口三十多萬,大約一半住
在不到半個(gè)月的時(shí)間里,奧密克戎就已經(jīng)侵?jǐn)_了全國大部分的縣城、鄉(xiāng)鎮(zhèn)乃至村莊。王玉蘭所屬的縣處于中部省份,常住人口三十多萬,大約一半住在城區(qū),一半生活在鄉(xiāng)村,城鎮(zhèn)化稍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GDP在省里排名中游,算是一個(gè)中規(guī)中矩的縣。面對突然造訪的奧密克戎,這里的反應(yīng)也可能是多數(shù)縣鄉(xiāng)的樣本。
縣城突然陷入病況,至今已過去近一個(gè)月,縣城和村莊里的人們經(jīng)歷了什么?他們?nèi)绾螒?yīng)對?當(dāng)多數(shù)人從第一次感染中痊愈之后,一切都好起來了嗎?

第一例
村莊的第一例陽性出現(xiàn)了,消息很快傳開。
病例出自于一位名叫王玉蘭的留守老人,兒子在外地工作,她和老伴留家照看兩個(gè)孫子女。一天夜晚,王玉蘭洗完澡,躺上床,突然感到喉嚨干得冒煙,一身骨頭酸痛,疼得下不來地。但挨到第三天,她也從未懷疑過感染的是新冠。
到了村大隊(duì)的診所,王玉蘭照常找村醫(yī)開藥,先測了一劑抗原,立馬顯示,“兩道杠!”村醫(yī)的表情變得可怖,緊張地說:“你站遠(yuǎn)一點(diǎn)!”之后連藥錢都沒敢收,一邊把人往門外請,一邊噴酒精殺毒。
王玉蘭走在回家路上,村民們原本的熱絡(luò)消失了,見面都躲得遠(yuǎn)遠(yuǎn)的,有的甚至撒腿跑開,“就跟看到了瘟人一樣。”
去年12月20日的中午,這一幕發(fā)生在江西省北部一個(gè)縣的村莊。村莊被大片的田地與山林包圍,在執(zhí)行了三年的疫情管控政策之后,許多村民早已達(dá)成共識(shí)——新冠是一種可怕的病毒。
王玉蘭曾在抖音上刷到一線城市感染的信息,有人說就是個(gè)小感冒,有人說疼得受不了,有人說要像產(chǎn)婦坐月子一樣,不能勞累,還不能洗澡。視頻五花八門,她不知道該信哪一種,還沒來得及對病毒形成足夠的認(rèn)知,也沒有任何防備,自己就突然成了村莊里確診的第一例。
在不到半個(gè)月的時(shí)間里,奧密克戎就已經(jīng)侵?jǐn)_了全國大部分的縣城、鄉(xiāng)鎮(zhèn)乃至村莊。王玉蘭所屬的縣處于中部省份,常住人口三十多萬,大約一半住在城區(qū),一半生活在鄉(xiāng)村,城鎮(zhèn)化稍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GDP在省里排名中游,是一個(gè)中規(guī)中矩的縣。面對突然造訪的奧密克戎,這里的反應(yīng)也可能是大多數(shù)縣鄉(xiāng)的樣本。
奧密克戎雖然在北方走過了一遭,但科學(xué)的信息還沒有及時(shí)傳遞到這座中部縣。當(dāng)病毒第一次出現(xiàn)在身邊時(shí),無知與擔(dān)憂依然是這里許多居民的第一反應(yīng)。
王玉蘭確診的這一天,縣城也迎來了感染的高峰。奧密克戎要走完這座縣城并不難,主城區(qū)不大,從北邊老舊的汽車站,到南邊通車不到8年的高鐵站,不過是20分鐘的車程。高峰期的城區(qū)里,許多飯店、超市、麻將館都拉上了卷簾門,街道一片空蕩。
王玉蘭感染后,不知道病毒傳給孩子會(huì)變成什么樣,晚上只好一邊戴著口罩,一邊睡覺。縣城里另一位居民,開始全天戴著KN95口罩,突然有一天,也有了頭暈想吐的癥狀,以為是病毒攻進(jìn)了體內(nèi),就把口罩摘下來。結(jié)果不一會(huì)兒,難受感消失了,她才意識(shí)到,自己不是感染,而是缺氧。
隨著奧密克戎在當(dāng)?shù)貍鞑ィ迩f里的人尤為緊張,大家都躲進(jìn)了屋子里——要看病的不去醫(yī)院了,治療甲狀腺、高血壓的藥物得省著吃,有的把兩片減成一片;菜園地也少有人去了,樹上的麻雀變得囂張,把白菜葉子啄得不像樣;下河洗衣服的人更少了,老人在家里不習(xí)慣地用起洗衣機(jī),聽著機(jī)器每天吵得嗡嗡響。就連雞和狗都藏在院墻里。一名村婦說,那段時(shí)間,她下河洗過一次衣服,除了過往的一兩輛汽車,路上連一只家畜都看不到。
村莊里,最極端的自我隔離發(fā)生在村民王華身上。因?yàn)閾?dān)心病毒傳給老人和孩子,他在出現(xiàn)癥狀之后,立馬躲進(jìn)了山里的一所小屋主動(dòng)隔離。
小屋的來歷緣于三年前,那時(shí),病毒還是第一次在武漢出現(xiàn),全國許多村莊實(shí)行嚴(yán)密管控,王華的老父親在城里做環(huán)衛(wèi)工,因?yàn)榻佑|垃圾太多,村民擔(dān)心他沾上病毒,執(zhí)意不讓他進(jìn)村,老頭只好在山里臨時(shí)搭起一個(gè)小屋。
說是一座房子,其實(shí)更像個(gè)牛草窩——沒有水泥墻,只圍了一圈干草,再用幾塊門板支撐,沒有床,老頭就拉來一張舊沙發(fā),夜里蜷縮在上面睡覺。時(shí)值隆冬臘月,夾著濕氣的冷風(fēng)從干草里灌進(jìn)來,被子摸起來潮乎乎的,蓋再多都不頂用。老頭不知是醒還是睡,在小屋里熬了二十來個(gè)夜晚,才等到村莊解封。
三年疫情,縣城經(jīng)常下通知臨時(shí)封控,最長一次又是十幾天。碰上這個(gè)情況,老頭回不了家,就不得不光顧小屋。去年10月,隆冬又降至,老頭擔(dān)心再受凍,于是請來水泥匠、磚瓦匠,給小屋籬了四堵墻,還專門買來一個(gè)水泵,把井水抽到山上去,方便洗臉和擦澡。計(jì)算下來,包括用料、工匠、水電,一共花費(fèi)了5000元,相當(dāng)于老頭兩個(gè)半月的工資。
沒料到,工程竣工不滿百天,政策就完全放開了。這一次,兒子王華想依靠小屋提供一些庇護(hù),主動(dòng)住進(jìn)去隔離。但效果全無,奧密克戎最終感染了全家。如今,小屋完全失去了效用,被廢棄在山林里。“5000塊就這么打了水漂。”老頭嘆著氣說。
高峰日
事實(shí)上,在許多縣城人的理解中,他們不懂什么叫“新十條”,也不懂政策哪一天放開,但對于2022年12月5日,他們卻有著強(qiáng)烈的共同記憶。
在那一天之前,縣城實(shí)行了最近一次的三天靜默。但到了5號(hào)夜里的10點(diǎn)多鐘,工人們突然出現(xiàn)在街頭,拆除形形色色的護(hù)欄。三年來,一到封城的時(shí)候,藍(lán)色的鐵皮、黃色的木板,像一塊塊膏藥一樣,貼在縣城的大街小巷。但這一次,拆除的形勢是那么地“毅然決然”,一直持續(xù)到下半夜,輪到一個(gè)居民家樓下的時(shí)候,已經(jīng)快天亮了。
這個(gè)居民早上起來一看,黑色的塑料編織帶,連同鐵管,都消失了。“不需要特別的通知,拆了肯定是自由出入,這已經(jīng)成了約定俗成的規(guī)矩。”他為暫時(shí)的自由而感到雀躍,一早就把卷簾門拉起,開始做生意。
在這個(gè)縣里,旅游業(yè)是支柱產(chǎn)業(yè)之一。因而,比起外出務(wù)工,更多人選擇留在本地做生意,依托旅游業(yè)而生。縣城結(jié)束靜默之后,生意人都盼望盡快燃起煙火氣,但好不容易開張了兩三天,奧密克戎到訪,把氣焰迅速掐滅。
大約在20號(hào)左右,縣城達(dá)到了感染的高峰。麻將館最先感受到了訊息,這里濃縮著一個(gè)縣城的小江湖,也是許多縣城人的精神依托。空閑的時(shí)候,縣城人或打發(fā)時(shí)間,或拓展人脈,或鞏固人情,都離不開一張麻將桌。自從病毒抵達(dá)縣城之后,門店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冷清,機(jī)器徹底停了半個(gè)月,落上一層灰。到了高峰期,老板干脆遣散所有員工,鎖上店門,回家躺了一個(gè)多星期。
在同樣的時(shí)間段里,奧密克戎也掃過了縣城的菜市場。這里是維持縣城生活更必要的一個(gè)基本單位,全民核酸取消后,攤主作為重點(diǎn)人群,依然需要落實(shí)“三天一檢”。但沒過多久,賣蔬菜的攤面先傳出了陽性,之后是賣魚肉和家禽的鋪面,陸續(xù)有人開不了攤,給攤位封上白色的塑料皮。
“今天我陽,明天他陽,上十天都是這樣。”一名年輕的攤主說,他預(yù)料到奧密克戎遲早有一天要來,擔(dān)心傳給家里人,于是早早地訂了一個(gè)小房間,感染全程都在外頭住。
類似年輕攤主的選擇并不少見,賓館老板因此迎來了生意。縣城中醫(yī)院附近,一家賓館老板聽聞感染人數(shù)暴漲,迅速嗅出商機(jī),推出5天隔離套餐,提供給那些陽性后不敢回家的年輕人。單人單間,定價(jià)880元,含每日三餐和跑腿代購服務(wù)。賓館老板說,3年疫情,門店一直冷清,沒想到在這個(gè)當(dāng)口看到了人氣。套餐推出后,入住率很高,幾乎每天都滿房。
相比于以上普通場所,學(xué)校作出了更快的反應(yīng)。這座縣城一共有兩所高中,面對這一波奧密克戎,它們做出了共同的應(yīng)對:重點(diǎn)保障高三生留校,高一與高二早早放假,回家上網(wǎng)課,期末考試也隨之推遲到下個(gè)學(xué)期。
葉明是其中一所高中的數(shù)學(xué)老師,也是高三年級(jí)的班主任。他不緊不慢地介紹,高三原本分為走讀和住校,但去年12月7日之后,學(xué)校采取了半封控措施,所有走讀學(xué)生必須帶著被子,住進(jìn)學(xué)校。
為了降低感染風(fēng)險(xiǎn),教室、宿舍、食堂,每日早、中、晚三次噴灑消毒水,以期殺死看不見的奧密克戎。但咳嗽的聲音還是出現(xiàn)了,首先在一個(gè)體育特長生的喉間發(fā)出,奧密克戎只用了兩三天時(shí)間,就傳遍了他班上的所有同學(xué),之后又在其他班級(jí)大面積傳播。
最終,高三一共27個(gè)班級(jí),1700余人,基本全部被感染。許多同學(xué)發(fā)高燒后,只好請假回家去,留在課堂的人變得稀稀落落,有的班級(jí)學(xué)生走光了,有的還剩下幾位在堅(jiān)持。對于后一種情況,老師照樣得來教室上課,在一股濃厚的消毒水味道里,老師感到教室像被霜打過了一樣,“班級(jí)一下子空了”,講課也變得沒什么激情。
到了22號(hào),學(xué)校原本安排了一次高三聯(lián)考,但有一半同學(xué)沒有完成考試,有的發(fā)燒后勉強(qiáng)考了一場,有的連一場都沒有參加。面對這個(gè)情況,學(xué)校決定在聯(lián)考結(jié)束之后,給學(xué)生徹底放6天的假。
重要一環(huán)
奧密克戎抵達(dá)縣城之后,缺藥、缺血氧儀、缺呼吸機(jī),各種醫(yī)療資源擠兌,是大多數(shù)媒體共同關(guān)注的話題。一直到最近,媒體仍然在討論,“新冠到底怎么治,村醫(yī)和醫(yī)生展開論戰(zhàn)”,“大流行沖擊鄉(xiāng)鎮(zhèn),老人多,藥庫空”,“老去的農(nóng)村如何度過新冠寒冬”。
在感染奧密克戎后,去診所買藥、打針,是許多縣城人的第一選擇。不比在醫(yī)院,一位診所醫(yī)生,往往更加直接地面對著附近城鄉(xiāng)的患者。因而,診所醫(yī)生成為了縣城應(yīng)對這一波感染的重要一環(huán)。
52歲的王宏是我到訪縣城的一名診所醫(yī)生,自新冠管控放開一周后,他所在的一間二十平米診室,每天要接待上百號(hào)發(fā)熱病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前來輸液的患者。每天早上八點(diǎn),王宏拉開診所的卷簾門,患者就帶著一張焦急而痛苦的面龐跟著涌進(jìn)來。王宏先進(jìn)行簡單問詢:“你感覺哪里不舒服?”如果癥狀是持續(xù)嘔吐、發(fā)熱、咳嗽,用不著核酸或抗原,他會(huì)立即給出一個(gè)肯定的判斷,“就是感染了這個(gè)病,打幾天吊針看看吧。”
這種肯定的態(tài)度往往使患者感到放心,他們滿意地點(diǎn)頭接受了。
但在面對第一位新冠病人時(shí),王宏心里其實(shí)很忐忑,“摸不準(zhǔn)病程,新冠到底該怎么治?”在感染潮到來之前,王宏自己先陽了,癥狀只是咳嗽和發(fā)燒,但接觸的病人中,不少人表現(xiàn)為嘔吐、頭疼、胸悶,有的甚至持續(xù)半月還沒好,“所以到現(xiàn)在,我對新冠還談不上完全了解,只能對癥來處理。”
這間診所開設(shè)20多年來,輸液是王宏以往應(yīng)對流行感冒的主治方式,也是縣城人生病后的習(xí)慣性選擇。因而,在開出大同小異的處方后,王宏走進(jìn)配藥室,把透明的小瓶葡萄糖擺成一排,上面寫好病人的名字,根據(jù)略微不同的病癥,注射“利巴韋林”、“頭孢尼西鈉”、“維生素C”,大多是治療呼吸道感染和增強(qiáng)抵抗力的藥物。
在高峰抵達(dá)之時(shí),診所醫(yī)生確實(shí)經(jīng)歷了一段時(shí)期的“買藥難”。許多縣城人買不到藥,荒誕的故事就此發(fā)生了。有人轉(zhuǎn)而相信中草藥,八種品類混合熬成一大鍋,全家一人一碗,每天不間斷;有人相信的是土方,早上一碗生姜蔥段水,下午是酸臘梅(一種治流感的本地藥材)泡成茶,有病沒病都得喝;年輕一點(diǎn)的,更相信細(xì)胞的免疫力,有人發(fā)燒到39度,沒有退燒藥,就在床上硬躺著,讓細(xì)胞全心全意跟病毒打架。
所有品類的相信中,最為荒誕的一種來自于太陽。一位居民感染后,聽傳牙刷會(huì)引發(fā)二次感染,就把家里四口人的牙刷并排晾在陽臺(tái)上,以期讓陽光殺死病毒。
這些荒唐的舉措,當(dāng)然不能阻止奧密克戎肆虐的步伐。2022年12月的最后一天,盡管距離高峰過去了一周,王宏依然需要同時(shí)應(yīng)對十幾號(hào)病人。他的腳上像踩了兩個(gè)風(fēng)火輪,在配藥室、輸液室之間來回竄動(dòng),有時(shí)是給病人換吊瓶,有時(shí)是量體溫,有時(shí)是拔針頭。忙碌要一直持續(xù)到深夜十點(diǎn),那是王宏設(shè)定的下班時(shí)間。而在一周前,病人根本看不過來,關(guān)門還得再推遲兩個(gè)小時(shí)。
新的一年來臨后,王宏更大的壓力來自于許多胸悶、氣短的老人。這些老人來自更為沉默的農(nóng)村,走進(jìn)診所后,眉頭緊鎖,臉上掛著明顯的恐懼和擔(dān)憂。王宏擔(dān)心有的老人肺部已經(jīng)感染,但診所里沒有血氧儀,他只能取出一個(gè)老舊的聽診器,把圓圓的鐵片貼在老人胸口,聽一聽肺部的呼吸音,如果察覺出不對勁,就要建議他們盡快去醫(yī)院,進(jìn)一步拍CT檢查。
從近半個(gè)月的就診規(guī)律來看,王宏預(yù)感到,許多農(nóng)村老人還處于危險(xiǎn)的早期,“對有基礎(chǔ)病的老年人來說,未來是個(gè)很大的挑戰(zhàn)”。
在家熬著的老人
在和王宏聊過之后,我回到了最初王玉蘭所在的那個(gè)村莊。新年的第一天,太陽終于掃去了頭一天陰沉沉的霧氣。一位村民說,午夜時(shí)分,在慶祝元旦的煙花綻放過之后,村子里就有三位老人年齡達(dá)到90歲。
村子中部,王慧蓮今年剛滿九十,是三位高齡老人中最先出現(xiàn)癥狀的一個(gè)。她住在一間老舊的木頭房子里,身前緊挨著一張桌子,上面放著必要的紙巾、水杯和枇杷膏,以方便自己吃藥和咳痰。
最近,她整日閉著眼睛,沒神采地坐著,面色變得越來越蒼白,嘴唇也有些發(fā)紫。
王慧蓮回憶,病癥發(fā)作是在12月下旬的一天。她去縣城取了當(dāng)月的養(yǎng)老金,回家之后,就感到喉嚨里像粘了一塊東西,忍不住開始咳嗽。來探望她的女兒也咳嗽,她有些擔(dān)憂地對母親說:“可能是感染。”
到了夜里,咳嗽變得劇烈。王慧蓮把當(dāng)天吃下肚的都咳吐了出來,身上一邊發(fā)燒,一邊又凍得發(fā)抖,鬧得一夜沒睡覺。第二天早上,燒還是沒退,她感到腦袋又昏又疼,撐著床想爬起來,又跌倒下去。
家里沒有體溫計(jì),女兒不知道母親燒到多少度,不敢喂布洛芬,又聽傳言說,新冠不同于感冒,不管多少度,都得讓身體燒。于是,王慧蓮沒有吃退燒藥,后來燒到舌頭、嘴唇都開裂了,渾身不剩一點(diǎn)勁,連頭也抬不起來,喝水就靠一根吸管。
這次生病之前,王慧蓮一共住過5次院。她有一身基礎(chǔ)病,高血壓、膽囊炎,心臟也不太好,住院最嚴(yán)重的一次是因?yàn)樗ち耸帧_@一次生病,王慧蓮說什么都不肯再住院,惦記她的老房子,還惦記著兩只雞沒人喂。這幾年,她膽囊炎發(fā)作,身上也是又冷又燒,疼到站不住腳,但都在家里硬熬過來了。
縣城一所二甲醫(yī)院里,一名醫(yī)生最擔(dān)心這類在家熬的老人。因?yàn)闆]有年輕孩子陪護(hù)在身邊,許多老人沒有就醫(yī)的意識(shí),硬生生地在家里熬到重癥。這名醫(yī)生說,最近醫(yī)院就收治了一個(gè)重癥老人,才七十來歲,到醫(yī)院時(shí),肺部已經(jīng)全白了,內(nèi)臟多個(gè)器官也接近衰竭。最后,老人沒用呼吸機(jī),也沒有進(jìn)行搶救,家屬就放棄治療了。
與城市不同,鄉(xiāng)村老人生病都靠熬。很多老人沒熬過,因癌癥、心臟病、腦梗,死在新冠流行的這個(gè)冬天之前,王慧蓮活到了90歲,因而成了村子里第二老的老人。
盡管一頭短發(fā)也白了,又染了一身老年病,王慧蓮還保留著一股粗糲的生命力。她曾經(jīng)做過接生婆,村子里很多70多歲的老人都經(jīng)她的手來到人世。王慧蓮一共生了8個(gè)孩子,沒找過生婆,都是自己在房間里,拿一把剪刀斷臍,再爬起來喝一碗紅糖水,睡上一覺,生產(chǎn)就算這么過去了。
后來,她在老房子里操辦了丈夫的一場葬禮,又辦了子女的7場婚禮。剩下一個(gè)人之后,陪伴她的是一臺(tái)電視機(jī),夜里一個(gè)人看新聞、天氣預(yù)報(bào)和戲曲。近幾年,電視機(jī)老化了,換成一臺(tái)收音機(jī),打開之后,要把聲音調(diào)到最大,她才可以聽到里頭有人在唱戲。
這一次感染新冠之后,收音機(jī)安靜下來。王慧蓮在房間里,沒日沒夜地睡了兩天,后來睡到脊背發(fā)痛,就叫女兒一定要把她攙起來,去堂前的椅子上半躺半坐著。
發(fā)病第三天,熱度終于退下來,可咳嗽沒有停。一到下半夜,王慧蓮咳得越來越兇,氣息也越來越急促,到后面,一口氣被堵在胸口,沒辦法呼出來,她拼盡全力想讓氣從嘴里順出,于是不受控制地哼哈哼哈呻吟起來。
為了緩解母親的咳嗽,兒子從村醫(yī)那兒買來一盒消炎藥,花了60塊,吃下去卻不頂用。再后來,女兒又買了一盒枇杷膏,倒是有點(diǎn)效果,每次一咳嗽,王慧蓮就拿勺子舀一點(diǎn),咽在喉嚨里,胸口立馬變得松快,咳嗽也隨之減緩下來。
作為村莊里老一輩的人,王慧蓮還不懂什么叫奧密克戎,說起來,“沾了一股生寒氣”,意思是患了重感冒。發(fā)作七八天以來,除了喝一點(diǎn)面湯,她什么都吃不下,聞到肉味更是要嘔吐。在村莊里,老人吃不下飯是一個(gè)不好的訊號(hào)。
孤島養(yǎng)老院
在奧密克戎肆虐的這個(gè)冬天,除了鄉(xiāng)村,養(yǎng)老院是一個(gè)老人更為集中的高危地區(qū)。
距離王慧蓮所在村莊二十公里之外,在一片茶園地之間,坐落著一家小型養(yǎng)老院,里面一共住了二十五位老人,平均年紀(jì)超過八十歲。院長陳紅向我介紹,老人們都患有嚴(yán)重的基礎(chǔ)病,有的全身癱瘓,只能躺在護(hù)理床上;有的半邊癱瘓,摔了一跤之后,臥床長滿褥瘡;有的不僅患了糖尿病,而且雙目失明,大小便經(jīng)常拉在身上。
陳紅是一個(gè)年近四十的女人,2020年在老家開辦了這所養(yǎng)老院。疫情以來,養(yǎng)老院一直受到民政部門的嚴(yán)格監(jiān)管,堅(jiān)持的原則是,“非必要不接觸”。每一次,遇到家屬來探望,陳紅會(huì)嚴(yán)格查看核酸證明、健康碼、行程碼,至今沒有出過一次意外,把養(yǎng)老院平穩(wěn)地運(yùn)行了下來。
聽到管控政策放開之后,陳紅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jī)。養(yǎng)老院里只有一臺(tái)呼吸機(jī),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醫(yī)護(hù)資源。“如果出現(xiàn)一例,我這里就完全癱了。”她緊張地說。沒有絲毫猶豫,陳紅只能用最原始的辦法,把養(yǎng)老院鎖閉起來。她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目前的情況下,除了流動(dòng)的物資,一只狗都休想從養(yǎng)老院門口闖入進(jìn)來。
奧密克戎掃過縣城,養(yǎng)老院成了最后一座孤島。每天,陳紅給老人測三次體溫,喝生姜蔥段水。核酸依舊是天天做,陳紅從鎮(zhèn)上的衛(wèi)生院領(lǐng)取了大量試劑,采樣完成后,再送回衛(wèi)生院檢測。物資流動(dòng)則依托于院外的三名工作人員,他們會(huì)把樣本從養(yǎng)老院門口取走,也會(huì)統(tǒng)一購買蔬菜、藥物、生活用品,再送回同樣的位置。
每一次交接,陳紅都要等人完全離開之后,再經(jīng)過三道消毒,才敢把東西分配下去使用。
除了物資之外,陳紅最擔(dān)心的還是護(hù)工問題,五位阿姨也是接近六十的老人,沒有人手替換,已經(jīng)連續(xù)工作了一個(gè)多月。陳紅盡量做了一些合理調(diào)配,比如,所有老人洗臉、泡腳,被安排在統(tǒng)一的時(shí)間。老人比以往睡得更早,起得更晚,總有老人睡眠不好,不到5點(diǎn)就醒來,陳紅會(huì)輕聲安慰,“天氣這么冷,在床上多睡一會(huì)兒。”早飯也推遲了一個(gè)小時(shí),遇到天氣好的日子,老人吃過之后,分散在院子里曬太陽,護(hù)工只需陪著他們聊聊天,以此減少不必要的工作量。
三年疫情以來,養(yǎng)老院的封閉,使許多老人和親屬的距離被拉遠(yuǎn)了。陳紅最為感觸的是一位腦梗老人,全身癱瘓?jiān)诖玻畠涸谏钲诠ぷ鳎缓冒阉瓦M(jìn)養(yǎng)老院。去年冬天,女兒在深圳懷孕,擔(dān)心疫情回家不方便,就在外地過了一個(gè)年。到了今年冬天,寶寶已經(jīng)生了下來,如今兩個(gè)月大。女兒高興地跟爸爸說,是個(gè)小外孫,過年一定帶回來給他看。但沒想到,養(yǎng)老院在年前完全封閉了起來,見面又要再錯(cuò)過一年。
積年累月見不到家人,老人們都把陳紅當(dāng)成最信任的人。他們接收不到外界的訊息,不知道這一次新冠感染變成了什么樣。最初,陳紅向他們解釋,這個(gè)病就是感冒,叮囑他們要添衣服,千萬不能受涼。其中一位老人聽完之后,疑惑地問道,“既然是小感冒,怎么一個(gè)月來,沒有一個(gè)家屬來探望?”后來,陳紅干脆把奧密克戎形容得更為嚴(yán)重。她還寬慰老人,院內(nèi)人出不去,院外人也進(jìn)不來,“里面就是最安全的”。
封閉之下,老人們最在乎的無疑是春節(jié)。每一年的這個(gè)時(shí)節(jié),大部分老人會(huì)被親屬接回家,護(hù)工也會(huì)正常放假。養(yǎng)老院里,一般會(huì)留下九位回不去的老人,自從住進(jìn)了這一座白墻黑瓦的大房子,九位老人不曾再離開,養(yǎng)老院成了他們名副其實(shí)的家。
這一次,所有子女打電話來說,外面不安全,春節(jié)就留在養(yǎng)老院。沒有一個(gè)家屬來接,老人之間反而維持著一種平靜,一位老人灑脫地說:“大家都不用回家,一起這里過年也蠻好。”白天,他們都在院子里,圍爐一坐,有的打牌,有的談天,暫時(shí)沒有受到奧密克戎的攪擾。
但養(yǎng)老院的封閉和護(hù)工長期工作還能堅(jiān)持多久?這是陳紅最近一直顧慮的問題。去年12月28日,冬日的一個(gè)雨天,縣委副書記走訪了這家養(yǎng)老院,傳達(dá)的指令也是,“嚴(yán)防死守”。陳紅明白,養(yǎng)老院里的老人遲早可能感染,而她需要做的,就是盡量把時(shí)間推晚,避開第一波高峰,無論如何要讓老人先熬過這一個(gè)嚴(yán)冬。
等待春天
但總有老人熬不過冬天。春天還沒有到,村莊里送葬的鞭炮聲已經(jīng)先響了起來。
送走的是王慧蓮村子里年齡排在第三的老人,家就住在她的隔壁。老人名叫王金亮,在村莊感染的風(fēng)潮里,王金亮的侄子先陽了,后來侄媳婦也有了癥狀。他們都擔(dān)心傳染給老人。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沒辦法完全隔開,侄媳婦只能盡量避免,每天戴著口罩做飯,自己不再去客廳,讓小兒子三餐捧著一碗飯,多夾一點(diǎn)菜拿給王金亮。
除了心臟不太好,王金亮沒有其他基礎(chǔ)病,一家人都認(rèn)為,相比于王慧蓮,他肯定能過完這個(gè)冬天。但沒料到,反而是他走得最為突然。侄子還提到,離世的頭一天夜里,他幫王金亮全身擦洗了一遍,之后,老人在沙發(fā)上看了一會(huì)兒電視,到了10點(diǎn)才進(jìn)房睡覺。
第二天早上,侄子快7點(diǎn)鐘起來,進(jìn)王金亮房間一看,老人已經(jīng)斷氣了。王金亮一身干干凈凈的,所以也不用特別的收拾,直接穿著身上的衣服,被下午才到的殯儀館車輛接走了。
王金亮去世的這一天早晨,王慧蓮的情況稍微好轉(zhuǎn)了一些。她已經(jīng)有了吃東西的欲望,一口氣吃了小半碗蒸菜。“抵得上吃了仙丹下肚啊。”她激動(dòng)地說,自己喉嚨已經(jīng)好受了很多,人也來精神了。
一直到下午,送葬的喇叭吹起來,王慧蓮才知道隔壁老人去世了。村民們陸續(xù)來吊唁,席面上,他們探討起老人的死因。侄子開口說,“應(yīng)該不是感染,一點(diǎn)都不咳”;一位同樣上了年紀(jì)的老頭當(dāng)即表示不同意,“如果不是這個(gè)病,這次肯定會(huì)沒事”;一位年輕一點(diǎn)兒的說,“到冬天來,老人血管也縮起來,死亡就是多一點(diǎn)”;另一位接著說,“就跟養(yǎng)牛一樣的,冬天冷了,老牛都要死很多”。
談話一直持續(xù)到席面結(jié)束。但沒有核酸,也沒有CT檢查,村民們最終也難以給老人的死亡下定論。
隨著這名老人的逝去,縣城卻漸漸地在這一波奧密克戎的感染后恢復(fù)。麻將館重新開張了,只是客人還沒有很多;菜市場的攤面也恢復(fù)了,陸續(xù)有人出門來買菜;臨近春節(jié),也有人去逛商業(yè)步行街,開始準(zhǔn)備新年的衣物。
像經(jīng)歷了一場急癥,初愈的縣城,仍然有很多人感到心有余悸。有人開始討論,什么時(shí)候會(huì)發(fā)生二次感染;有人對信息有了更強(qiáng)的敏銳度,聽說一種XBB的新毒株,又立馬打電話給藥房,問是否能買到蒙脫石散;還有人在家里躲過了第一波,至今沒有感染,但心里戰(zhàn)戰(zhàn)兢兢。
因?yàn)闆]有核酸,村民們難以計(jì)算,村子里多少人躲過了這一波感染。唯一確定的是,山包腳下,距離最初那所林中隔離小屋的不遠(yuǎn)處,奧密克戎暫時(shí)放過了一所更為破敗的老屋。
老屋里,住著全村最老的老人,是一位獨(dú)居的老太,如今已經(jīng)95歲。丈夫去世多年后,她也變成孤零零的一個(gè)人,老到無法再出門。曾經(jīng)做過廚師的兒子住在她隔壁,每天送去一日三餐。
新年第一天,老太的兒子正在修繕一小扇籬笆門。算起來,他已經(jīng)大半個(gè)月沒有出門,每天頂多收拾一下屋門口的菜園地,因而還沒有感染。但這樣的自我封閉同樣無法持續(xù),再過一段時(shí)間,就要到除夕,兒子說,自己始終要出門買年貨,走親戚,不知道哪一天會(huì)把病毒帶回來,再傳到老母親那兒去。
村莊里,在經(jīng)歷了一位老人離世之后,村民們同樣為老太感到擔(dān)心。他們曾在吊唁的席面上討論,不知道奧密克戎什么時(shí)候會(huì)造訪那一間墻面脫落的老屋,悄無聲息地鉆進(jìn)老太的身體。
-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hào)禁止網(wǎng)民評(píng)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yùn)輸局對網(wǎng)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diào)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fù),很快便引起了社會(huì)大眾對于5個(gè)月前,深圳市交通運(yùn)輸局將及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hào)禁止網(wǎng)民評(píng)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yùn)輸局對網(wǎng)民申請公開北極鯰魚調(diào)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的回復(fù),很快便引起了社會(huì)大眾對于5個(gè)月前,深圳市交通運(yùn)輸局將及 -
 軍訓(xùn)順拐同學(xué)們組成了方隊(duì) 引發(fā)了網(wǎng)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xùn)順拐同學(xué)們組成了方隊(duì)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xùn)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wǎng)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duì)的隊(duì)伍。這支
軍訓(xùn)順拐同學(xué)們組成了方隊(duì) 引發(fā)了網(wǎng)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xùn)順拐同學(xué)們組成了方隊(duì)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xùn)場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景吸引了網(wǎng)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duì)的隊(duì)伍。這支 -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yàn)楣ぷ魈β刀箲],也聽說過有人因?yàn)楣ぷ魈y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yàn)榭臻e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nèi)卷加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yàn)楣ぷ魈β刀箲],也聽說過有人因?yàn)楣ぷ魈y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yàn)榭臻e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nèi)卷加 -
 網(wǎng)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wù)檢查2023-09-16 16:38:53據(jù)國家稅務(wù)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稅務(wù)局網(wǎng)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稅務(wù)部門通過分析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luò)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jīng)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網(wǎng)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 遂依法對其開展了稅務(wù)檢查2023-09-16 16:38:53據(jù)國家稅務(wù)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稅務(wù)局網(wǎng)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稅務(wù)部門通過分析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luò)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jīng)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
 恒大人壽嚴(yán)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fēng)險(xiǎn)處置再進(jìn)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fēng)險(xiǎn)處置再進(jìn)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jiān)督管理總局深圳監(jiān)管局官網(wǎng)公布《關(guān)于海港人壽保險(xiǎn)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xiǎn)有限公司保
恒大人壽嚴(yán)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fēng)險(xiǎn)處置再進(jìn)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fēng)險(xiǎn)處置再進(jìn)一步。9月15日,國家金融監(jiān)督管理總局深圳監(jiān)管局官網(wǎng)公布《關(guān)于海港人壽保險(xiǎn)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xiǎn)有限公司保 -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guān)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dāng)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shí),王耀慶卻因?yàn)楸瘋?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guān)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然而,當(dāng)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shí),王耀慶卻因?yàn)楸瘋? -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wǎng)站列入專項(xiàng)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quán)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jù)塔斯社15日報(bào)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wǎng)站將朝鮮國務(wù)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xiàng)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píng)稱,這是基輔政權(quán)的又一次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wǎng)站列入專項(xiàng)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quán)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jù)塔斯社15日報(bào)道,對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wǎng)站將朝鮮國務(wù)委員長金正恩列入專項(xiàng)人員名單,俄副外長加盧津批評(píng)稱,這是基輔政權(quán)的又一次 -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jù)荔枝新聞報(bào)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dāng)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jìn)行敲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jù)荔枝新聞報(bào)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dāng)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方多次對其座椅進(jìn)行敲 -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wù)部門通過分析發(fā)現(xiàn)袁冰妍存在涉稅風(fēng)險(xiǎn),經(jīng)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存在偷逃稅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wù)部門通過分析發(fā)現(xiàn)袁冰妍存在涉稅風(fēng)險(xiǎn),經(jīng)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存在偷逃稅 -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zhǔn)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xiàn)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wǎng)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zhǔn)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xiàn)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wǎng)友紛紛表示,沒有卓偉的日子,娛樂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